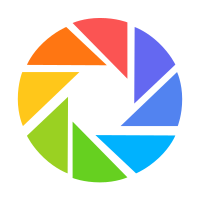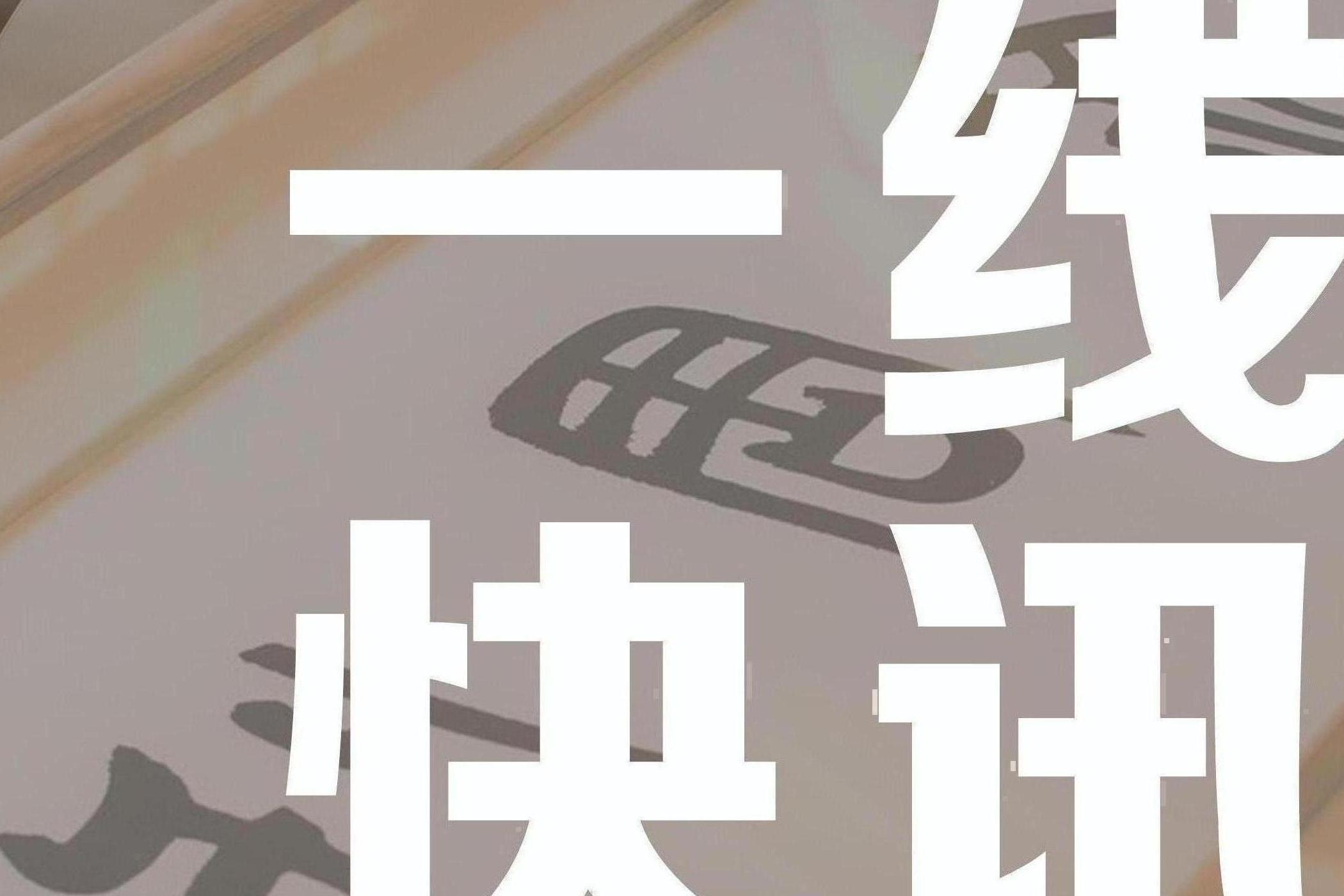公司创投惊喜过后意难平:北京中关村公司型创投税收政策的失与得

2021年1月7日,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官网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发改委、科技部、证监会、知识产权局等国家部委联合印发文件,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开展公司型创投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试点和技术转让所得税优惠政策试点。笔者在第一时间针对新公布的公司型创投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解读——《公司型创投迎重大利好,最高可减免100%企业所得税》

近日,笔者拿到了相关政策的全文——《关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公司型创业投资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试点政策的通知》(财税[2020]63号)(以下简称“63号文”),经过认真学习与研究,对63号文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考虑到63号文的政策制定背景,其政策目标应当是解决个人投资人投资公司型创投的税收待遇和合伙型创投相比存在较大差异,希望能够降低个人投资人的综合税负,鼓励和倡导长期投资理念。
在这方面,63号文确立了简单、易懂、易操作的标准,首次在公司型创投层面适用“流经原则”来解决双重征税问题,首次尝试将税收优惠政策和鼓励长期投资挂钩,以实现个人投资公司型创投的综合税负下调(最终效果大致为综合税负在30%~20%之间)。
但63号文也存在“流经原则”适用不彻底也不准确,将长期投资分为3年-5年两档稍显冗余,优惠对象不够精确,认定标准和条件较高且与其他优惠政策无法叠加的问题。
期待在后续政策落地和推广的过程中,能够继承优点,总结经验,通过公开征求意见引入多方意见群策群力,共同推进政策的完善并向全国推广,推动基金税制的完善,促进创投行业的发展。
以下为详细解读。
一、政策制定背景
自国务院2016年发布“创投国十条”——关于促进创业投资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53号文以来,鼓励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成为了一项社会共识,创投国十条所规划的蓝图目前正在一步步实现。
创业投资企业,或称创业投资基金,目前在中国主要以两种组织形式存在,分别为公司型和有限合伙型。从所得税税制上讲,两种不同的组织形式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课税逻辑和方式:
(一)公司型创投的课税逻辑和方式
笔者在《私募小乒乓系列99:公司型创投基金税收政策梳理及建议》一文中有详细说明。
大致为:
1.公司型创投存在基金层面(公司层面)和股东层面双重课税。基金层面征收企业所得税,股东层面根据股东类型分别征收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对于自然人投资于公司型创投而言,由于双重课税的存在,其综合税负大致可以认为是40%;
2.基金层面的企业所得税,按照应纳税额 = 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减免税额-抵免税额的公式进行计算。
3.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可以根据公式参数,分为,
(1)税基减免方案。如《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97条确立的: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的,可按照70%投资额抵扣应纳税所得额。
(2)优惠税率方案。如《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91条确立的:非居民企业取得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第(五)项规定的所得,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3)减免税额方案。如《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90条确立的: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第(四)项所称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是指一个纳税年度内,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本次财税63号文就行按照减免税额方案来进行制定的。
(二)有限合伙型创投的课税逻辑和方式
笔者在《私募小乒乓系列98:从创收税收优惠8号文解读创投个税迷思》一文中有详细说明。
大致为:
1.有限合伙型创投自财税[2008]159号文以来针对有限合伙企业确立了“准实体课税”模式,即参考“流经原则”(Pass-Through Principle),对合伙企业层面不课税,对合伙企业的法人合伙人穿透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合伙企业的个人合伙人穿透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于自然人投资合伙型创投而言,按照8号文最新确立的规则,其综合税负大致可以认为是20%或5~35%。
2.因有限合伙型创投,基金层面并不课税,所以相应的优惠政策是穿透至其法人合伙人或个人人合伙人来享受的。如财税〔2018〕55号所确立的:法人合伙人或个人合伙人可以按照对初创科技型企业投资额70%抵扣其从合伙创投企业分得的所得;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
3.有限合伙型创投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思路在此不予赘述。
从上述中我们可以分析出现在公司型创投和合伙型创投在税制上有颇多差异:
一是,对个人投资人而言,投资公司型创投和投资合伙型创投存在较大的税负差异。在不考虑特殊优惠政策的情况下,目前的综合税负大致是40%对20%。
二是,目前针对有限合伙型创投,已经出台了包括财税[2015]81号文、财税[2018]55号文,财税[2020]8号文等相关政策。而针对公司型创投,目前仅有55号文,相关的优惠政策很少。
三是,虽然在创投国十条中明确鼓励倡导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但目前无论是公司型创投还是合伙型创投中,尚未明确将长期投资和税收优惠制度相挂钩的机制安排。
为了解决公司型创投的税收待遇问题,鼓励长期投资理念,2020年9月5日夜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北京市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工作方案的批复》(国发[2020]123号文),正式同意由北京市政府及商务部提交的《工作方案》申请,批复允许组织实施。在《工作方案》中,国务院同意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开展公司型创投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试点。在试点期限内,对符合条件的公司型创投企业按照企业年末个人股东持股比例免征企业所得税,鼓励长期投资,个人股东从该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具体条件由财政部、税务总局商有关部门确定。北京市财政局在关于印发《北京市财政局“两区”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中明确将于2020年年末出台相应政策。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公司型创业投资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试点政策的通知》(财税[2020]63号)。
二、政策制定思路及方案
从政策的制定背景中和国务院的有关公告中我们不难看出,本次63号文的拟定可能有两个核心要点:一是要解决个人投资者在公司型创投和合伙型创投中存在较大税负差异的问题;二是要在税收优惠政策中落实鼓励长期投资理念。
我们首先来看63号文的核心内容:
“对示范区内公司型创业投资企业,转让持有3年以上股权的所得占年度股权转让所得总额的比例超过50%的,按照年末个人股东持股比例减半征收当年企业所得税;转让持有5年以上股权的所得占年度股权转让所得总额的比例超过50%的,按照年末个人股东持股比例免征当年企业所得税。
上述两种情形下,应分别适用以下公式计算当年企业所得税免征额:
(一)转让持有3年以上股权的所得占年度股权转让所得总额的比例超过50%的:企业所得税免征额 = 年末个人股东持股比例×本企业年度所得税应纳税额÷2
(二)转让持有5年以上股权的所得占年度股权转让所得总额的比例超过50%的:
企业所得税免征额 = 年末个人股东持股比例×本企业年度所得税应纳税额
……
个人股东从公司型创业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政策制定的核心思路在于:
1.将公司型创投的所得分为股权转让所得和股息红利所得,穿透适用不同的税制。对股息红利所得部分,个人股东在个人征税环节缴纳个人所得税。针对股权转让所得部分,通过落脚到减免企业所得税的方式来设计优惠政策;
2.根据股权转让所得的具体情况,认定减免公司型创投层面的企业所得税,且为按照年末个人股东持股比例减免企业所得税,而非穿透至个人征税环节减免个人所得税;
3.符合减免情形的核心标准在于:转让持有的股权的所得,占年度内股权转让所得总额的比例,是否超过50%;
4.为鼓励长期投资,按照转让持有股权的持有年限(3年;5年两档),区分为减半和免征两档。
三、政策制定效果
我们先来说63号文好的一面:
1.标准简单,易懂,易操作。无论是适用对象的条件,还是减免情形的认定,标准都比较简单、易懂、易操作,降低了申请机构的实操成本,提高了对于申请政策支持的市场预期。
2.尝试在公司型创投层面适用“流经原则”。其一在于区分公司型创投获得的所得类型,可分为股息红利所得和股权转让所得。将两种不同的所得进行区分,适用不同的税收政策;其二在于针对股权转让所得部分,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可减半或免征企业所得税。
3.尝试将税收优惠和长期投资挂钩,以鼓励长期投资理念。主要在于符合减免情形的核心标准拟定为转让持有特定年限的股权所得占全年股权转让所得的比重需超过50%。
4.尝试将个人投资公司型创投的综合税负下调。从目前的政策来看,按照满足63号文的最低和最高要求,个人的综合税负大致在20%~40%之间。
不过笔者经过一番思考和研究之后,认为63号文目前仍有一些不妥之处:
1.“流经原则”的适用并不彻底,也不准确。
其一,如果严格适用“流经原则”,应当最终确立在公司创投层面(基金层面)不缴税。而本次是“减”“免”两种情形,而不是单一的“免除”的情形。
其二,如果严格适用“流经原则”,应当最终确立将公司创投层面所有的收入、支出、亏损根据相应的性质(如股权转让所得;股息红利所得)穿透到个人层面进行汇算清缴(在个人层面进行收入、亏损的抵消后征税,如股息红利所得按照《个人所得税法》适用20%的税率,股权转让所得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财产转让所得适用20%的税率)。但因为我们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法》暂未将个人的财产转让所得纳入综合所得,也未推出资本利得税这一税种,故强行穿透确实“水土不服”。本次只是折衷的,仍然在公司层面进行汇算清缴。个人层面仅依照穿透后的所得性质和比例判断是否达到减免条件,不进行汇算清缴。
其三,如果严格适用“流经原则”,还需考虑公司当年收益是否全部分配给投资者的要件。按照美国市场形成的惯例,为避免“流经原则”被滥用于恶意避税,公司在适用“流经原则”时一般还需要配合一个兄弟原则,叫“打钩原则”(Check-The-Box Rule)。“打钩原则”是指,如果企业按照公司组织形式设立,但将当年收益全部分配给投资者并由投资者缴税的,可适用流经原则作为免税主体,由投资者直接承担纳税义务。如果企业按照合伙企业组织形式设立,但是当年度收益不向投资者进行分配,应当否定其免税主体身份。缺乏“打钩原则”的约束,只要公司层面不进行分配,投资者就不会产生纳税义务,在此条件下豁免公司层面的企业所得税,可能会导致出现一些原本不属于创投行业的机构和业务,出于避税的冲动进入到行业中,造成一些混乱。
2.将长期投资分为3年、5年两档,似无必要。
其一,从“流经原则”的精神来看,如最终要解决的是在公司层面不交税,那么直接规定“免除情形”是较为合适的,无需规定“减半情形”。在123号文中也只是提到了“免除企业所得税”,并未提及“减半”的事宜。
其二,区分为“3年”、“5年”两档,不光使得政策和123号文预期的效果打了将近5折,实操层面在收集材料和认定情形方面也变得更加复杂,对申请机构和税务征管机关而言成本倍增。
其实,可以考虑将3年-5年两档合并为一档,即转让持有超过4年的股权所得占当年度股权转让所得占50%以上,即可享受免除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3.优惠对象不够精准,容易引发争议。
其一,按照123号文中提及的“按照企业年末个人股东持股比例免征企业所得税”原则,我们可以分析出63号文主要是为了降低个人股东的综合税负。但因为落脚点却放在了减免公司创投层面的企业所得税上,因此优惠政策的对象并不精准。
其二,对象不精准就导致了优惠的力度直接和公司年末个人股东的持股比例成正比,比例越高,力度越大。可能会导致:(1)个人股东扎堆成立基金,不愿意和企业、机构投资人共同成立基金;(2)部分机构会试图在年末突然增加个人股东的持股比例,在享受优惠政策后又降低个人股东持股比例的方式来实现恶意避税;(3)在个人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的公司创投中,优惠力度过小,无法精准为该个人股东降低税负。
其三,在个人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的公司创投中,由于降低了企业所得税,法人股东实际上享受到了同等的优惠。一般而言,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是,个人股东希望未来在分配环节适当向个人股东倾斜,但企业股东并不愿意(如大部分国有企业应该都无法同意在分配环节向个人股东倾斜)。
4.认定条件仍然较高,且与其他优惠政策无法叠加,最终优惠力度不足
其一,优惠力度和多个指标有关,即和个人股东持股比例有关,也和转让股权的持有年限有关,同时也和占当年度股权转让所得的比重有关,认定条件比较复杂也比较高。
其二,因63号文的优惠条件是针对公司创投层面的企业所得税减免,没有穿透到个人环节,那对于个人股东而言最大优惠情形下,仍然需要承担20%的综合税负。而当叠加财税[2018]55号文时,55号文对于公司型创投也是抵扣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额(而非穿透至个人环节抵扣个人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额),最高也是可以达到减免企业所得税的效果,等于和63号文相互重合了。最终对于个人股东而言,最大优惠仍然是承担20%的综合税负。而对于个人投资合伙型创投而言,其直接的综合税负大概为20%或5%~35%,但如果叠加财税[2018]55号文时,其个人纳税环节可以进行应纳税所得额的抵扣,那么最大优惠可以做到免征个人所得税,因而最大优惠个人承担的综合税负是0。这样来看,63号文给予给个人投资者的优惠力度就显得不足了。
四、总结与反思
(一)简化认定标准的思路值得肯定
目前63号文在认定“符合条件”的创业投资企业上标准非常简单直观,所设定的减免情形的标准也非常简单直观,利于市场和税收征管机构的理解和操作,有助于优惠政策的实际落地。
(二)鼓励长期投资理念的举措值得推广
63号文首次在税收优惠政策中引入鼓励长期投资理念的设计,这对于真正从事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的创投机构而言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也有助于中国市场上的资金逐渐转化为耐心资本,真正从事和助力长期的、富有价值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创新创业事业。
(三)在试点过程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为政策推广打下实践基础
相信63号文的出台目的是为了解决个人投资者在公司型创投和合伙型创投中税负存在较大差异,公司型创业被抑制发展的现状。而从笔者的前文中可以发现,其实63号文目前存在一些漏洞和不足,可能会导致这一政策目标难以实现,能够有效保护中小个人投资者利益的公司型基金的发展仍然会收到很大局限。在63号文的试点过程中,我们可以去观察笔者的拙见是否准确,结合实际情况,总结经验和教训,为下一步政策修订、推广打下坚实的实践基础。
(四)政策制定及修订过程中可引入公开征求意见的机制
财税政策作为影响一个行业发展的基础性政策,其在制定和修订的过程中引入公开征求意见机制,能够帮助行业迅速理解政策制定意图,充分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市场经验,帮助政策制定机构完善政策内容,精准地实现政策目的。希望未来在63号文进一步修订和推广的过程中,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征求市场专业机构和专家学者的意见,群策群力共同推动创投财税政策的完善,助力创投行业高质量发展。